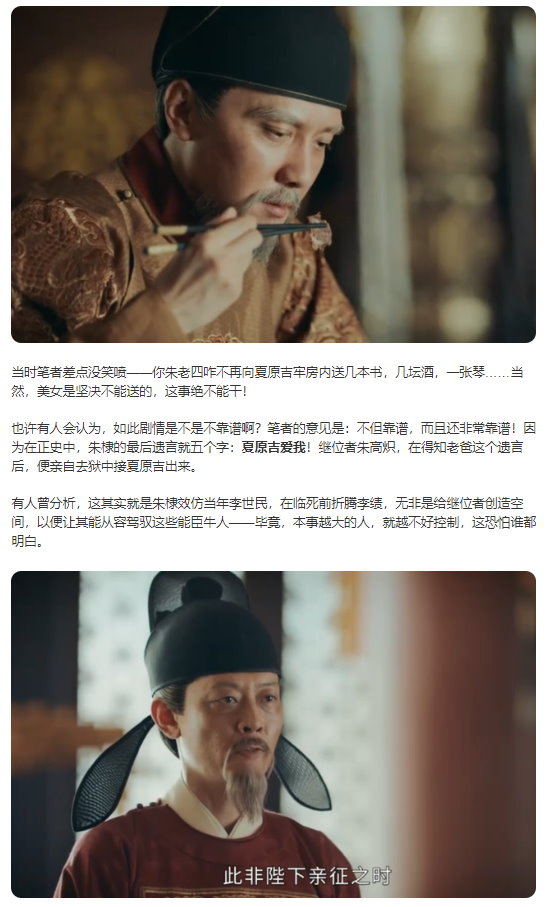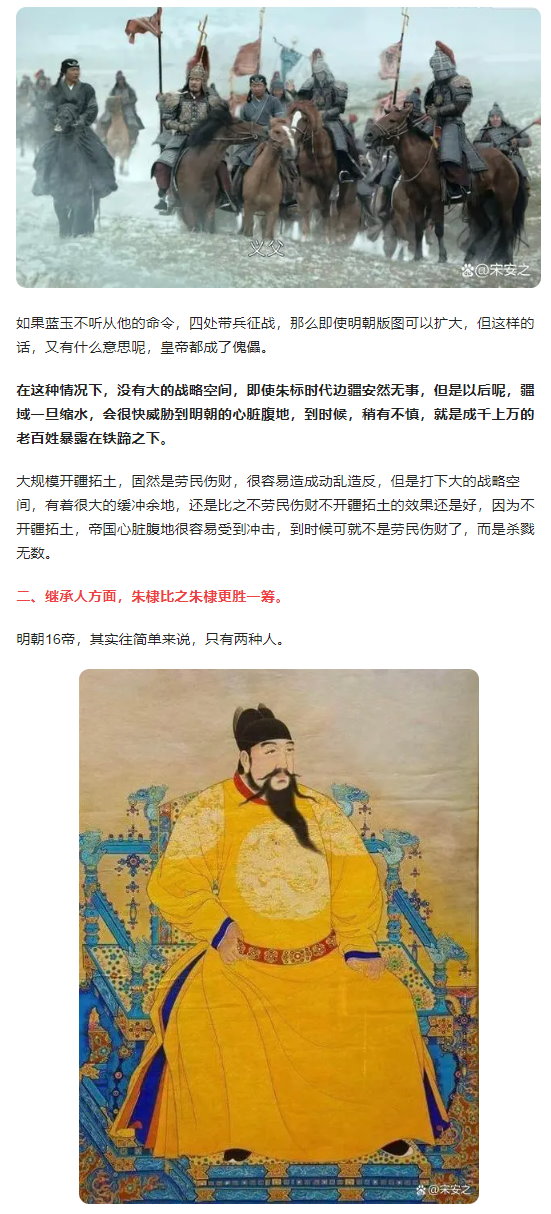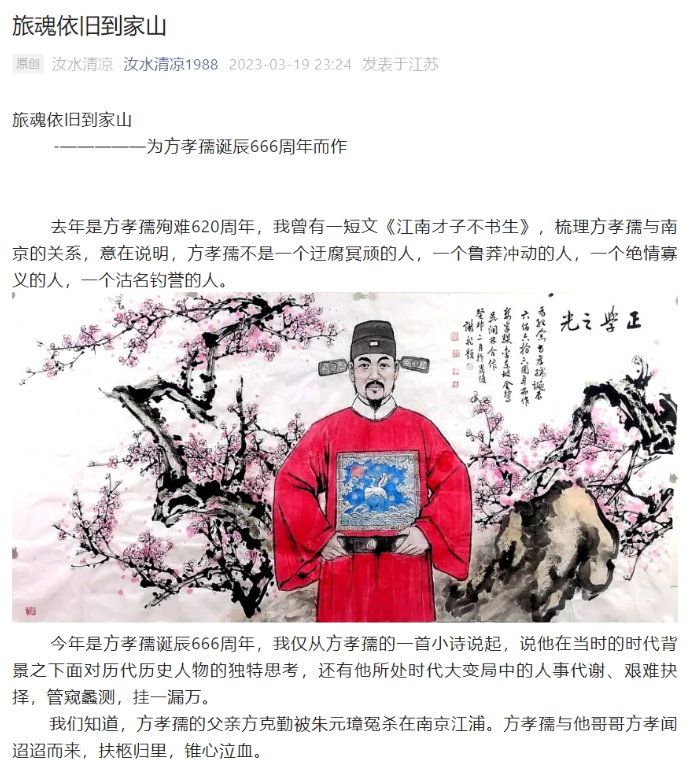明惠帝失踪疑案:
兼谈揭开疑案的徐作生
* 柯木林 *
《联合早报》 1995-06-13/14 (星期二/三)
兼谈揭开疑案的徐作生
* 柯木林 *
《联合早报》 1995-06-13/14 (星期二/三)
1399年,燕王朱棣为夺取帝位,起兵北平,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“靖难之役”。1402年,燕兵攻陷京师(今南京),燕王即位,是为明成祖,当时皇宫一片火海,明惠帝(建文帝)朱允炆不知去向,成了历史上一大悬案。
明惠帝到底去了哪里?他是否死于火?还是逃亡在外?这个问题不仅长期困扰着明成祖,也困扰了后来的数代皇帝,五百多年来,更成为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。
明惠帝不知所终
明成祖在位时,对惠帝的踪迹一直耿耿于怀。永乐年间,成祖派心腹大臣四出访察,有的是明言出使,有的则扮成普通百姓,秘密寻找惠帝下落。私访惠帝最著名的大概是胡荧了。胡荧官至户科给事中,相当于今日的公安部长,在明成祖在位的20余年间,他一直奉行搜索惠帝。郑和下西洋也有察访惠帝的用意,在郑和的使团中就有锦衣卫特务人员跟随,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。明神宗对惠帝的下落也颇感兴趣,万历年间,神宗诏访惠帝一案,此时距“靖难之役”已170多年了。即使在明朝灭亡之后,于1739年(乾隆四年)刊行的《明史》中,也留下了“(惠)帝不知所终”的记载,可见数百年来,人们对惠帝的去向,都不断地作出种种努力,试图揭开这桩疑案的真相。
明惠帝遁入空门
历史不负有心人,明惠帝的踪迹近年来终于有了落案。上海《文汇报》编辑徐作生,原是学历史出身的,自1983年起迄1990年,
他利用七年的时间,检阅大量史料和方志,又赴吴县、南京、北京实地考察,寻访明惠帝遗迹。在他数次前往江苏吴县鼋山穹窿山一带进行勘访时,在此找到了惠帝
出亡的遗迹遗物,如雕龙柱础、御池、御池桥、神道、方石等。徐作生以文献材料结合实地考察,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:当年明惠帝出亡后,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
济寺内,不久,转移阵地,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,直至1423年病殁于此,葬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。由此可见明惠帝没有死于火,而是遁入空门,出家为僧了。
惠帝陵前的御池桥,至今仍然保存良好。
明惠帝出亡遗迹之一,皇驾庵柱础上的雕龙,清晰可见。
然而,惠帝是怎样逃出南京的?这位逊国之君在当年如此紧锣密鼓的追捕下,其形踪又如何得以保密呢?这一连串的问号,给明史增添神秘色彩,五百年来使人们一直难穷其究。
怀着考史的一种偏执,徐
作生从浩瀚史料中,理顺出这样的逻辑:当京师失陷时,明惠帝束手无策,想蹈火自尽,后经群臣劝阻,于是剃去头发,披上黑色僧服,乘着星夜从聚宝门(今中华
门)逃到了神乐观。在神乐观住上一宿,然后沿着水关御沟(地下水道)潜行,漏夜逃离南京。从南京逃出后,由水路乘小舟进入太湖,被溥洽藏匿于鼋山普济寺。
溥洽是明惠帝的主录僧,惠帝出逃时剃发为僧,即出自溥洽之手。他因知道惠帝逃跑一事而被成祖禁锢了11年。奇怪的是,溥洽在普济寺被捕,燕兵在苏锡常一带包围搜捕,却不见惠帝踪影。当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护人来相助,惠帝形踪必定暴露!那么,这个神秘的保护人又是谁呢?
“无冕宰相”姚广孝
根据徐作生的考证,此人
就是姚广孝,长洲(今江苏吴县)人。他是明成祖的心腹谋士,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无冕宰相”。在辅佐成祖夺得帝位后,功成身退,归隐禅寺。明惠帝藏匿于鼋山
普济寺,姚广孝是一个知情人,并且曾经与惠帝见过面。未几,事机败露,溥洽被他的一个同僚告了密,被捕入狱,而姚广孝则出于良知,把明惠帝转移到他的佛地
之内。(姚广孝以成祖赦赐名义,将穹窿山划归为他的佛地,山内不得居民)。
姚广孝卒于永乐十六年(1418年)三月,临终前,还特地从吴县穹窿山远赴北京,在成祖面前求情,保释因惠帝出亡一案而受累下狱的溥洽。不难想象,当姚广孝殇后,穹窿山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具有严密的防范措施,明惠帝的安全也失去了有力的保证。于是,惠帝的踪迹就在姚广孝逝世的第二年(永乐十七年,1419年),被胡荧发现了。
胡荧力保惠帝
至此,徐作生大胆假设:当胡荧知道惠帝的行踪后,在成祖面前力为开脱,以免惠帝一死。成祖也不想杀害这个甘心遁入空门,不与世争的皇侄,以免落得违逆天意,杀侄篡位的恶名,胡荧力保惠帝之举,也正和他的“宽厚,喜怒不形于色”的性格相符合。
胡氵荧最后一次向成祖报告,是在永乐二十一年(1423年)。当天深夜,胡荧由外地回朝,直奔皇宫,其时成祖已入睡,听到胡荧来朝,立即披衣接见,并谈到“四鼓乃出”。胡荧与成祖交谈了什么?他俩为什么半夜三更才谈完?这是历史留予后人的一段曲笔…
徐作生就看出其中奥妙,他由此推断:胡荧最后一次的报告,乃是有关惠帝殁亡之事。“惠帝殁亡之日盖在永乐二十一年,时年46岁。”这也正与《明史》所载吻合。史载,明成祖直到临死前一年(成祖殁于1424年)才对惠帝一案放下心来。另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是:郑和连续六次下西洋后,成祖从此就再也没有让他出使。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在宣德五年进行的(1430年)。这不应被视为一种偶然的巧合,而是与不必再访察惠帝有着内在的联系。
既然前人对惠帝踪迹之研
究似已有了“定论”,徐作生怎么还会想到再去考证惠帝一案呢?他当时的思路是怎样的?他怎么会想到惠帝是出亡穹窿山而不是踪迹云南呢?徐作生的考证与前人
论证的最大不同之处,是他找到了惠帝陵,以及惠帝出亡的实物史料。根据历史记载,明惠帝死后,成祖曾以“天子礼敛葬”,但南京却没有惠帝的陵墓,徐作生又
为何能确定穹窿山的小山丘,当地百姓历来称之为“皇坟”的土堆,就是惠帝陵呢?
我与徐作生素昧平生,1994年8月,我在海南岛旅次,闲来无事,在新华书局购得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晁中辰的名著《明成祖传》来阅读,从而知道了徐作生考证明惠帝出亡穹窿山的论证。回到上海后,托友好与徐作生联系,但缘悭一面,后来才知道他因病住院。同年12月我再次专程到上海拜会他。1994年12月12日上午,徐作生与其夫人到我下榻的虹桥宾馆来看我,我们相叙甚欢,当下,我就向徐作生提出我的疑问。
500年历史悬案终揭开
徐作生说,他寻访惠帝踪迹的最大考虑,是“在近不在远”。试想,永乐年间,成祖曾多次榜示天下,对出家人进行监控。在这严密搜捕之下,惠帝及其随臣若爬山涉水,千里之行,行踪必定容易败露;再者,事隔100多
年后的万历年间,神宗诏访惠帝一案时,有关惠帝出亡的书籍如《从亡随笔》、《致身录》及《逊国臣记》等,俱在苏州吴县一带问世,而西南或中原各地未见这类
书籍。在检阅大量史料和方志时,徐作生又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,那就是明、清《苏州府志》、《吴县志》上所说的“积翠庵,一名皇驾庵”,实误。根据徐作生
考证,皇驾庵即拈花寺,惠帝陵就在拈花寺后。张郁文《木渎小志》记载道:“明建文帝逊国时曾移驾于此。”沿着这条线索,徐作生数次到穹窿山实地勘察,终于
揭开了这500多年的历史悬案。
“皇陵”头上动土自找麻烦?
在谈到如何确定惠帝陵时,徐作生说,拈花寺后的皇坟,在坟顶上原置有一块正方形大青石,是为陵墓的标识。当地30岁以上的村民都是见证人。可惜这块大青石,文革期间,为当地农民从坟顶推下山脚,裂成两块,被当作建筑材料,砌在宅基之下,这位农民在次日就暴毙了,因此当地村民迷信说这是翻动皇陵的惩罚。
惠帝陵墓顶的一块大青石,已被当地农民砌成宅基。
穹窿山的惠帝陵,当地村民称为“皇坟”。
徐作生说,他本人曾研究
过古代帝陵的形制。古人认为,天是圆的,地是方的,许多皇帝的陵寝砌成上圆下方的形状,以附会“天圆地方”之说。明代帝陵的主体建筑为宝顶和方城,宝顶即
圆形墓之顶,方城是宝顶前面的部分。置于穹窿山皇坟顶上(宝顶)的这块方形陵碑(方城),再配上附近的御地、御池桥、神道等,这种简单的帝陵形制,正与
“备天子礼敛葬”一语吻合。更何况从文献史料中,没有任何记载显示历史上有其他帝皇埋葬于此。徐作生因此判断,此乃惠帝陵。而惠帝陵是按照成祖的旨意去做
的。
普济寺成采石场
徐作生的论证,真是无隙
可击。在我的提议下,他欣然答应带我重访明惠帝遗迹。我们在吴县穹窿山那寂寥人烟的山区内,登上了皇坟宝顶,拍摄许多御池、御池桥、神道、雕龙柱础等惠帝
出亡遗迹。当然,惠帝最终的隐匿处皇驾庵(拈花寺)是荡然无存了。我们也不辞旅途劳累,找到了鼋山普济寺遗址,这是溥洽最初藏匿惠帝的地方,亦是溥洽被捕
之处。可惜当年的普济寺,如今已成为采石场工地,寺庙被拆毁一空,但在原址上仍可寻觅到许多柱础。
徐作生现年46岁,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,现为《文汇报》编辑,是个业余的青年历史学家。20多年来,除了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外,常于斗室钻研文史,或负笈远涉考察。
徐作生除了探讨明惠帝的
下落外,对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、古麻刺宝山烽堠等悬案,都有创见和新的提法,尤其在考证古麻刺朗国这一悬案上,他所撰写的《南洋何处“古麻刺朗”》一文,
得到菲律宾前任总统阿奎诺夫人的赏识,称赞他“为菲中友谊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”。(徐作生考证古麻刺朗国在今菲律宾棉兰老岛,其国都即棉兰老岛西南岸
海港城市库马拉朗。)
此外,徐作生还参加了《中国文化之谜》、《千古之谜》、《中国历史三百题》三本书的编写工作。由于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,上海历史学会、郑和研究会、中外关系史学会先后接纳他为会员或研究员,他还应邀出席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。
我之认识徐作生,明惠帝可说是主要牵线人,若干年后,徐作生当与明惠帝齐名。明史研究者在提及惠帝一案时,就不得不想到徐作生——这也正是他多年刻苦钻研的代价,历史是不会辜负徐作生的。
今日头条 - 明朝大才子解缙,惨死锦衣卫之手,他的书法告诉我们低调很重要
https://www.toutiao.com/i6706497925867897358
今日头条 - 朱棣当年到底有没有找到朱允炆?这位大臣或许给出了答案
https://www.toutiao.com/i6708567801872777739/
今日头条 - 建文帝朱允炆真的逃出南京城吗?朱棣的谎言骗了我们六百年!
https://www.toutiao.com/i6735567888226189831
《联合早报》- 两次大逃亡——明初华人逃亡三佛齐 与拜里米苏拉逃亡新加坡 (2021-02-18)
朱元璋称帝后,杀害开国功臣胡惟庸,导致大量华人流亡三佛齐。三佛齐新王拜里米苏拉因庇护这些流亡华人,不愿继续效忠爪哇,爪哇军队因此攻打三佛齐,拜里米苏拉逃来新加坡……
1368年,在开国功臣拥戴之下,朱元璋在南京登基,国号大明,号称洪武帝。
朱元璋坐上帝位后,没忘记舍生忘死的战友,除了赐封爵号外,也在南京鸡笼山建功臣庙。
这些开国功臣浑身是胆,太子朱标却温良敦厚,朱元璋担心,太子无法驾驭这群豪杰。为了朱氏皇朝不受威胁,朱元璋决定大开杀戒。
胡惟庸深得朱元璋信宠,1373年任右丞相,后擢升左丞相——这是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的职位。胡惟庸后来日益跋扈,结党营私,独断专行,引发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权力冲突。
华民流亡三佛齐国
1380年,朱元璋受邀到胡惟庸府邸,途中太监云奇冒死阻拦,朱元璋回头登上城墙,看见府内埋伏士兵,指胡惟庸谋反将他处死。此后,朱元璋不再委任丞相,设立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,这使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上。
胡惟庸案接下来的十几年继续发酵,从意图谋反发展到私通三佛齐。
朱元璋将各种罪名套在胡惟庸身上,结果众多开国功臣都被牵连,诛杀三万多人。
蓝玉案是明初另一大案,牵连被杀的有一万多人。严从简《殊域周咨录》提到:“自胡惟庸谋乱,三佛齐因而遣间谍绐我使臣羁留于境。爪哇国王闻知其事,戒三佛齐,令其礼送还朝。后诸国道路不通,商旅阻绝。”
在三佛齐掳掠使节的都是华人,他们是胡惟庸等案的受害者,或是其他原因,仇视明朝,在洪武年间大量逃亡到三佛齐避难。这些海盗最负盛名的是陈祖义,他祖籍广东潮州,拥有百艘战舰,党羽过万。马欢在《瀛涯胜览》指出:“他甚是豪横,凡有经过客人船只,辄便劫夺财物。”当时明朝悬赏50万追捕陈祖义。
《明史》记载:“今欲遣使谕爪哇国,恐三佛齐中途阻之。闻三佛齐本爪哇属国,可述朕意,移咨暹罗,俾转达爪哇。”1397年,暹罗使者传递朱元璋信息,要求爪哇派遣使者告诫三佛齐,诚能省愆从善,则礼待如初。
三佛齐新王叛变
《明史》记载,三佛齐国王怛麻沙那阿者曾在1373年入贡,他在1376年(洪武九年)逝世,隔年王子遣使入贡,使者言:“嗣子不敢擅立,请命于朝。”《明史》载:“天子嘉其义,命使臣赍印,敕封三佛齐国王。时爪哇强,已威服三佛齐而属之,闻天子朝封为国王与己埒,则大怒,遣人诱朝使邀杀之。天子亦不能问罪,其国益衰,贡使逐绝。”
三佛齐新王企图通过明朝赐封获得独立,爪哇老王无法容忍三佛齐和自己平起平坐,派人将中国使者杀害。当时爪哇国势强盛,朱元璋也无可奈何,三佛齐则继续受爪哇统治。
《东方志》(Suma Oriental)同样记载老王和新王,他进一步指出,新王拜里米苏拉(Parameswara)娶爪哇国王侄女为妻,老王死后继承王位。马六甲灭国后,葡萄牙人皮雷斯(Tome Pires)于1512-1515年间居住马六甲,期间又去爪哇、苏门答腊和马鲁古等地,收集马来苏丹王国的资料,对马六甲王朝建国的历史了解透彻,并完成巨著《东方志》。
爪哇当时处于满者伯夷王朝,国家分而治之,国王哈奄武禄(Hayam Wuruk)的王后没有男后裔,他在1389年逝世后,女婿继承王位统治西爪哇,这就是《明史》记载的西蕃王。
拜里米苏拉的妻子则是哈奄武禄侄女,他开始觉得自己身份尊贵,不比爪哇西蕃王低微。
胡惟庸之乱导致大量华人流亡三佛齐,在当地形成举足轻重的社群,他们掳掠朝贡使节和商船,并且获得统治者的庇护。拜里米苏拉觉得三佛齐比爪哇强盛,不愿继续效忠爪哇西蕃王。虽然朱元璋只要爪哇告诫三佛齐,但叛变之心毕露,因此爪哇决定派兵攻打。
三佛齐灭国之灾
《东方志》记载,在丹绒普汀国的协助下,爪哇新王御驾亲征。三佛齐是苏门答腊岛的古国,国都在今天的巴淋邦(Palembang,华人称为巨港或旧港)。爪哇军队先攻打隔邻的邦加岛,杀了1000人,接着登陆三佛齐。三佛齐新王带领6000人迎战,最终不敌爪哇的军队,部属成为俘虏。拜里米苏拉预先安排家眷和随从在船上,眼见无法和爪哇军对抗,自己逃上船只扬帆离去。
《明史》记载:“时爪哇已破三佛齐,据其国,改其名曰旧港,三佛齐逐亡。国中大乱,爪哇亦不能尽有其国,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据之。”《殊域周咨录》则说:“其后爪哇并三佛齐,废其国。其地有旧港,商舶所聚,爪哇置小酋以司市易。南海人梁道明弃乡里来居,积岁聚众,为之酋长。”
梁道明原籍广东南海,洪武癸酉年乡贡进士。最初南下贸易,熟悉当地民情后举家迁居。当时旅居该处的数千闽粤华人,群起拥梁道明为王。永乐三年(1405),明成祖派人招安,梁道明于11月回国,留下副手施进卿驻守。
三佛齐沦陷后,拜里米苏拉逃来新加坡,八天后杀死统治者自立为王。他的随从在此种植大米和捕鱼,或是掠夺敌人船只为生。《东方志》记载,新加坡曾经被满者伯夷占领,当时的统治者是暹罗(阿瑜陀耶)国王的女婿,他迎娶王妃(北大年重臣之女)所生的公主为妻。国王得知消息后,派北大年重臣率领军队前来,拜里米苏拉不敢应战,和随从逃亡,他占据城邑已有五年。
永乐赐封马六甲国王
拜里米苏拉来到马六甲,《明史》记载:“永乐元年(1403)十月遣中官尹庆使其地,赐以织金文绮、销金帐幔诸物。其地无王,亦不称国,服属暹罗,岁输金四十两为赋。”
马六甲古称满剌加,受阿瑜陀耶控制,拜里米苏拉是一方头目,因此必须向暹罗缴纳税金。明朝如此重视拜里米苏拉,正因他是巨港统治者,庇护华人海盗抢掠朝贡使节和商船,他在新加坡期间继续掠夺来往船只。尹庆出使马六甲,宣示威德及招徕,其意在于招安,以确保贸易海道的顺畅。拜里米苏拉遣使随庆入朝贡,其使者言:“王慕义,愿同中国列郡,岁效职贡,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。”永乐帝封他为马六甲国王,并赐他国印,在中国皇帝撑腰之下,他从此摆脱泰国的枷锁,实现建国的梦想。
朱棣临死前做一怪梦,对杨荣说:莫非天不佑大明?25年后果然应验
https://mbd.baidu.com/newspage/data/landingsuper?rs=1399348127&ruk=nkbo0VRWwWeCxHJ3oVhojw&isBdboxFrom=1&pageType=1&urlext=%7B%22cuid%22%3A%22livJigahHugHuHit_avVtlin2aYmaHaKgOSqfl8TSig38HfWYa2Kt08lWMlP8Sud9bHmA%22%7D&context=%7B%22nid%22%3A%22news_8599243877542923105%22%7D
朱棣夺位后,在皇宫发现一密旨,哭着喊道:父皇,你害的我好苦
https://mbd.baidu.com/newspage/data/landingsuper?rs=3267800541&ruk=nkbo0VRWwWeCxHJ3oVhojw&isBdboxFrom=1&pageType=1&urlext=%7B%22cuid%22%3A%22livJigahHugHuHit_avVtlin2aYmaHaKgOSqfl8TSig38HfWYa2Kt08lWMlP8Sud9bHmA%22%7D&context=%7B%22nid%22%3A%22news_9532086159956016276%22,%22sourceFrom%22%3A%22bjh%22%7D
太子朱标英年早逝,帝系转移朱棣一脉,对明朝来说反是一件大好事
https://mbd.baidu.com/newspage/data/landingsuper?rs=708762012&ruk=nkbo0VRWwWeCxHJ3oVhojw&isBdboxFrom=1&pageType=1&urlext=%7B%22cuid%22%3A%220P24aY8mv80zivt_g8HOf08BSug6av8PgavCiladvilkiv8UgaSPilfX3a0r8QMhb9UmA%22%7D&context=%7B%22nid%22%3A%22news_9302586463566035416%22,%22pushToVideo%22%3A%22newPush%22%7D
旅魂依旧到家山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tPORAqkkqZqu0r9R9ZsBOg
一代妖僧,姚广孝
https://www.xiaohongshu.com/explore/6589308e000000003c010dcb?app_platform=ios&app_version=8.21&author_share=1&share_from_user_hidden=true&type=normal&xhsshare=WeixinSession&appuid=6583a801000000001b032ea5&apptime=1704946721
朱棣造反成功,发现父皇圣旨,痛哭:你害我好惨
https://mbd.baidu.com/newspage/data/landingsuper?rs=2892830077&ruk=nkbo0VRWwWeCxHJ3oVhojw&isBdboxFrom=1&pageType=1&urlext=%257B%2522cuid%2522%253A%2522giS6t_abHi_3uvuFlaHIt_8MvalfiS8G0u2ZuguaSalha2ukgiB_8gt2Qar_kWMHzb1mA%2522%257D&context=%7B%22nid%22%3A%22news_8908071310438623958%22,%22__INVOKE_TYPE_KEY__%22%3A%22__INVOKE_TYPE__%22,%22pushToVideo%22%3A%22newPush%22%7D
明朝第一迷案被揭开:建文帝朱允炆被发现,原来他在此地终老
https://mbd.baidu.com/newspage/data/landingsuper?rs=253263914&ruk=nkbo0VRWwWeCxHJ3oVhojw&urlext=%7B%22cuid%22%3A%22082DujO32iYj82uAg8-Yu_ukSagzi-uO_uSfijuMvi0SOviKgaSTu_is3ur5iSRCHPtmA%22%7D&isBdboxFrom=1&pageType=1&sid_for_share=99125_1&context=%7B%22nid%22%3A%22news_9725282357439941082%22,%22sourceFrom%22%3A%22bjh%22%7D
明朝第一谜案被揭开:建文帝朱允炆踪迹查明,原来他在此处终老
https://mbd.baidu.com/newspage/data/landingsuper?urlext=%257B%2522cuid%2522%253A%2522082DujO32iYj82uAg8-Yu_ukSagzi-uO_uSfijuMvi0SOviKgaSTu_is3ur5iSRCHPtmA%2522%257D&rs=4063056262&ruk=nkbo0VRWwWeCxHJ3oVhojw&like_icon_type=2&isBdboxFrom=1&pageType=1&sid_for_share=167054_4&context=%7B%22nid%22%3A%22news_9569909630681811133%22,%22__INVOKE_TYPE_KEY__%22%3A%22__INVOKE_TYPE__%22,%22pushToVideo%22%3A%22newPush%22%7D
雨打芭蕉,滴答作响。栖霞山深处的古寺里,一盏孤灯在风中摇曳。我抚摸着手中那本泛黄的古籍,指尖微微颤抖。
明初,靖难之役后,建文帝朱允炆突然人间蒸发,史书上仅寥寥数语——"火焚宫殿,帝不知所终"。四百余年来,这个谜团困扰着无数学者。
有人说他在大火中灰飞烟灭,有人说他削发为僧远走天涯,更有人说他逃往海外再未归来。
当我翻开那本落满尘埃的日记,看到第一页上那枚残破的玉印,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,终于要揭开它神秘的面纱。建文帝,原来一直在那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终老……
"师父,这《永乐大典》残本上的批注是您所写吗?"我放下手中的茶盏,看着院中伏案沉思的老僧。晨光透过竹帘洒在他枯瘦的身上,如同镀了一层金边。
老僧没有抬头,只是轻轻抚过那残破的纸页,嘴角泛起一丝难以察觉的苦笑:"吾心有惑,不得不察。这注解乃先师所留,非我所能为。"
"可这批注里提到的建文帝失踪细节,史书上从未记载啊。"我忍不住追问。
老僧终于抬起头,那双饱经沧桑的眼睛直视着我:"小友,四百年前的建文之谜,至今无解。你既专攻此道,可曾想过,历史的真相,往往隐藏在字里行间之外?"
我叫林墨,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,专攻明史,尤其是建文帝朱允炆失踪一案。三个月前,我的导师偶然提起栖霞山上有一位精通明史的老和尚,据说收藏了不少珍贵史料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我来到了这座名为"不二庵"的偏僻古寺。没想到,这一住就是整整一季。
老和尚法名悟元,据说已有九十高龄,却目光如炬,思维敏捷。更令我惊讶的是,寺中藏书丰富得惊人,不少都是海内孤本,其中关于明初历史的记载,甚至比正史还要详尽。最让我震惊的是,悟元师父对建文帝朱允炆的事迹了如指掌,谈起来如数家珍,仿佛亲眼所见一般。
"小友,你知道建文四年那场大火的真相吗?"一天傍晚,悟元师父忽然问我。此时夕阳西下,余晖映照在他的脸上,给那张饱经沧桑的面孔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
"史书上说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,但民间传说他逃出宫去,从此销声匿迹。"我如实回答。
"史书记载,皆为胜者所书。"老僧轻叹一声,"世人都说建文帝已死,可民间却有无数传说,说他出逃为僧。有人说他去了西藏,有人说他去了云南,甚至有人说他远赴海外,辗转流离。你对这些传说,怎么看?"
"学界对此争论不休。"我斟酌着回答,"有人认为这些都是野史杜撰,但也有学者相信建文帝确实逃脱,只是无法确定他去了哪里。我的博士论文正是研究这个问题。"
老僧微微一笑,那笑容中似乎包含了某种深意:"历史如河,表面平静,暗流汹涌。真相常藏于细微之处。小友既然有心研究,何不随我去一个地方?"
雨季的江南,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。薄雾缭绕在山间,仿佛把整座栖霞山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中。我跟随老僧穿过寺院后的竹林,拾级而上,来到一座隐蔽在悬崖峭壁间的石室前。石室门扉斑驳,上面刻着"不二法门"四个古朴的篆字,字迹已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。
"这里是我寺祖师闭关之所,五百年来,鲜有人至。"悟元从怀中取出一把看似普通却做工精细的青铜钥匙,"今日破例,只因你与此事有缘。"
我心跳加速,不知为何,总觉得即将揭开一个重大的秘密。石门缓缓开启,发出沉闷的呻吟声,一股夹杂着檀香和陈旧纸张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。室内光线昏暗,只有透过石壁上的一个小孔射入的一线阳光,照亮了中央的一方石桌。石桌上端坐着一尊佛像,佛像前供奉着几样简单的祭品。
但最引人注目的,是墙角那个上锁的乌木箱子。
老僧轻轻走到木箱前,从怀中取出另一把钥匙,打开了箱锁。随着"咔嗒"一声轻响,那个看似普通的木箱被打开了。老僧小心翼翼地从中取出一叠用丝绸包裹的泛黄纸张,递给我。
"这是?"我小心翼翼地接过,发现那是一本手写的日记。打开第一页,只见纸张虽已泛黄,但保存完好,上面的墨迹依然清晰可见。
"一代君王的心事。"老僧意味深长地说。
日记的第一页写着"洪武三十一年夏",正是建文帝即位的时间。我的心跳顿时如擂鼓一般,难道这真的是建文帝的亲笔日记?如果属实,这将是一项足以震惊学术界的重大发现!
"师父,这日记从何而来?确定是建文帝所写?"我激动得声音都在颤抖。
"先读完再说。"老僧示意我继续翻阅,他的表情异常严肃,"读完后你自会明白。"
我小心地翻开日记,逐页阅读起来。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建文帝即位后的心路历程,他的改革计划,对削藩的犹豫与决心,以及对各方势力的担忧,特别是对叔父燕王朱棣的戒备。文字间流露出一个年轻君王的理想与忧虑,以及肩负国家重任的压力。
"洪武三十一年七月,今日早朝,听闻燕王朱棣又增兵马,心中不安。祖制严明,诸王不得干政,然燕王素有野心,恐怕不会甘心就此屈居藩地。"
"洪武三十一年九月,今日与黄子澄商议削藩之事。子澄言燕王势大,当徐徐图之,不可操之过急。吾思来想去,觉其言有理,然朝廷大权不可旁落,终须有所行动。"
随着靖难之役的爆发,日记的语气变得越来越紧张,字迹也开始潦草,透露出作者当时的不安与恐惧。
"建文四年五月,燕军势如破竹,已攻占济南。齐泰、黄子澄等皆主战,然朝中主和之声亦不绝于耳。吾夜不能寐,常思祖训,不知何去何从。"
"建文四年六月,北报频传,燕军已过淮河,直扑应天。朝中人心惶惶,不少大臣已暗中投诚于燕王。吾知大势已去,然国祚不可轻弃,当与燕王一决雌雄。"
最后几页记载了南京城破前的情景,字迹颤抖,透露出极度的恐惧与绝望:
"建文四年七月初三,燕王兵临城下,大势已去。徐辉祖战死,忠臣良将所剩无几。众臣劝吾自焚以全社稷尊严,然吾不忍就此而亡。四海之大,难道容不下一介布衣?今夜,将由贴身太监徐景昌引路,微服出宫,剃度为僧……若有来世,愿再为明君,不负天下苍生。"
我震惊地抬头看向老僧:"这意味着建文帝并未在宫火中身亡,而是成功出逃了?"
老僧点头:"继续读下去,答案就在其中。"
我翻到下一页,发现记载的地点已经变成了南京城外的一座小庙:"建文四年七月初五,今藏身于城南清凉寺。徐景昌言外间传闻宫中大火,皇后及宫女皆葬身火海,燕王已宣布我死于火中。如此也好,或可免除追捕。然想到皇后及宫中无辜之人,心如刀割。我朱允炆,虽为天子,却未能保全至亲,枉为人君!"
日记继续记载,建文帝在南京城外的寺庙中躲藏了数日,后来听闻朱棣派人四处搜寻可疑的僧人,他便不断转移,足迹遍布江南各地。
"建文四年八月,今已剃发为僧,法名净寂。徐景昌言燕王已登基,改元永乐,并大赦天下,唯独不赦'建文余党'。今日听闻方孝孺及其九族被诛,心如刀绞。方先生忠义之气,青史留名,而我却只能隐姓埋名,苟且偷生,愧对忠臣!"
"建文四年十月,今转至杭州灵隐寺。此地香客众多,易于藏身。闻永乐帝已下令彻查天下寺庙,搜寻可疑僧人。吾须再转移,思之再三,当取道西南,前往更远之地。"
日记中的建文帝一路西行,经过湖广、四川,行程艰辛,几度险象环生。
"永乐元年春,今至成都青羊宫。此地道观林立,官府难以一一查访。然近日忽闻有密探入蜀,搜寻'建文余党',心中不安,当尽快离去。"
我翻到最后一页,发现记载戛然而止于永乐二年:"永乐二年冬,今已至云南大理。路途遥远,跋山涉水,备尝艰辛。幸得当地一杨姓土司收留,暂得安身。然燕王——不,永乐帝之爪牙无处不在,吾当继续西行,或取道缅甸,前往更远之地……"
"师父,这日记后来为何中断了?建文帝最终去了哪里?"我合上日记,抬头望向老僧,眼中满是疑惑。
"因为,后面的内容太过惊人。"老僧从木箱底层取出另一本更为破旧的册子,"这是第二部分。"
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第二本日记,发现记载的时间已经是永乐十年,也就是建文帝出逃六年后。纸张明显比第一本更为陈旧,字迹也有所变化,但仔细辨认,依然能看出是同一人所写。
"永乐十年春,吾已游历大半个江南,又西行至云贵川等地,几度险遭永乐帝派出的密探擒获。思来想去,唯有远离中原,方能保全性命。今决定取道西南,前往滇地深处。滇地多少数民族,官府势力薄弱,或可藏身。"
随后的记载显示,建文帝一路西行,经过湖广、四川,最终到达云南深处。在那里,他遇到了一位姓杨的土司首领,对方认出了他的身份,却并未告发,反而提供庇护。
"永乐十一年秋,杨土司告诉我,他曾是建文朝的进士,对我父子有恩。他说,永乐帝虽已坐稳龙椅,却仍在全国搜捕'建文余孽',尤其是对我的下落格外关注。杨土司建议我暂居云南,待时局平稳后,再做打算。"
"这与民间传说吻合!"我兴奋地说,"确实有说法称建文帝逃到了云南,甚至有'木兰夫人'的传说,说建文帝在云南娶妻生子。"
"但真相远不止于此。"老僧神色凝重,"往后读。"
日记记载,建文帝在云南住了三年,期间学习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和习俗,甚至娶了一位当地女子为妻。然而好景不长,永乐十四年,朱棣派兵进入云南,征讨当地"不臣之民",实则是在搜寻建文帝的踪迹。
"永乐十四年冬,永乐帝派大军入滇,名为征讨叛乱,实为搜寻我的下落。杨土司告诉我,朝廷已有密报,疑我藏身云南。为保安全,我不得不再次启程。此去万里,只愿寻得一处清净之地,了此残生。杨土司建议我随商队,取道缅甸,前往天竺。彼处远离中土,又有佛法盛行,适合隐居。"
我惊讶地合不拢嘴:"建文帝去了印度?这在正史中完全没有记载!"
老僧微微一笑:"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。继续看下去。"
接下来的日记详细记载了建文帝的印度之行。他随商队经过缅甸,穿越崇山峻岭,历尽艰辛,终于抵达了北印度。在那里,他住进了一座佛寺,专心研习梵文和佛法。
"永乐十六年春,今已至天竺北部,居于一座名为'鹿野苑'的佛寺中。此地乃佛祖初转法轮之所,香火鼎盛。寺中僧人多通汉语,我谎称是中土来的求法僧人,倒也无人起疑。每日诵经礼佛,倒也清闲自在。只是每当夜深人静,想起中土亲人,不免黯然神伤。"
"永乐十七年夏,今日听闻有中土商队到访。我刻意避而不见,恐被认出。然经由寺中僧人之口,得知中土近况:永乐帝已迁都北京,大兴土木,修建紫禁城;又派郑和下西洋,威名远播。不得不承认,叔父确是一代英主,治国有方。若当年我能早些看清形势,或许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"
我震惊地看着这些文字,难以置信建文帝对朱棣竟有如此评价。"他对朱棣,似乎并无太多怨恨?"我抬头问道。
老僧意味深长地说:"失去皇位的痛苦,或许反而让他看清了许多事。继续读下去。"
日记显示,建文帝在印度住了近三十年,期间精通梵文,研习佛法,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高僧。他还记录了印度的风土人情、宗教礼仪和社会状况,这些内容对研究明代中印文化交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
"永乐二十二年,闻永乐帝已崩,朱高炽继位,改元洪熙。吾已出走十八载,鬓发皆白,昔日君王,今成异邦孤僧。世事沧桑,不过如此。每思及当年与叔父的争斗,皆因各执一端,不肯退让。如今看来,不过是一场大梦。"
"仁宗朱高炽是个仁君,建文帝为何不选择回国?"我问道,"按理说,朱高炽对他应该没有敌意。"
"因为他已看透了权力的本质。"老僧叹息道,"皇位之争,从来不是儿戏。即使朱高炽对他无恶意,朝中依然有无数受永乐帝提拔的大臣,他们会容忍'亡国之君'的回归吗?继续读下去。"
日记继续记载,洪熙帝在位仅一年就驾崩,其子朱瞻基继位,改元宣德。宣德年间,建文帝曾萌生回国之念,但最终还是放弃了。
"宣德三年,今年已六十有三,在天竺已度过二十余载。每逢月圆之夜,望着同一轮明月,便思念故土。然细思之下,回去又能如何?即便不被发现,也不过是苟活于市井之中,倒不如在此清修,了此残生。"
"宣德十年,今日得知宣德帝已崩,其子朱祁镇继位,改元正统。算来,我那侄孙已是第五位皇帝了。时光荏苒,曾经的恩怨情仇,如今想来,不过是过眼云烟。"
日记显示,正统年间,中原连年灾荒,蒙古屡次入侵,朝政混乱。建文帝在印度听闻这些消息,心中不忍,终于决定回国。
"正统五年,闻中原连年灾荒,蒙古屡次入侵,心中不忍。吾已六十有八,鬓发如霜,今欲踏上归途,再看故土一眼,了此夙愿。虽不能为国分忧,但或可在民间行些善事,聊表寸心。"
这是日记中最后的记载。我翻遍了整本日记,再也没有找到后续内容。
"师父,建文帝最后回国了吗?他去了哪里?怎么没有继续记录了?"我急切地问道。
老僧沉默片刻,起身走到石室的一面墙前,轻轻推开一块看似普通的石板,露出一个隐蔽的暗格。从中取出一个精美的檀木小匣,打开后,里面是一枚翠玉雕琢的玉印和一封用丝绸包裹的泛黄信笺。
"这是……"我惊讶地看着那枚玉印,小心翼翼地拿起来,借着微弱的光线,看清了上面刻着的"建文"二字。
"建文帝的御玺,真品。"老僧肃穆地说,"而这封信,是他回国后写给一位故人的。"
我的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,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封信笺。信纸已经发黄,边缘有些破损,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,与日记如出一辙:
"景昌吾弟:
别来二十载,音讯全无,不知汝可安好?吾已从天竺归来,现隐居于栖霞山下一小庵中。此地远离尘嚣,松涛竹影,颇适修行。吾年已七旬,已看透人间沧桑,无意再涉世事。然每思故国,不免黯然。闻正统帝年幼,国事多艰,朝中奸佞当道,边患频仍,不胜忧虑。吾虽无力回天,然每日诵经念佛,但愿国祚绵长,百姓安康。
余已返回故土,隐居于江南一隅。此生已无牵挂,唯愿在这方水土上,安度余年。朱氏江山已非吾念,但望天下百姓,能享太平盛世。他日若有明史修撰,吾之生平,不必详述。让建文四年成为一个谜,或许是最好的结局。
景昌若有闲暇,可来栖霞山不二庵一叙。吾日日盼之。
允炆手书于栖霞山不二庵
正统六年春"
信的落款是"允炆",旁边盖着那枚建文玉印,印记清晰可见。
"这……这太不可思议了!"我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,"这意味着建文帝确实活着回到了中国,而且就隐居在栖霞山?"
"不仅如此。"老僧指着信笺的最后一行小字,那里写着"栖霞山下,不二庵"。
我瞪大了眼睛:"不二庵?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寺院吗?"
老僧点点头:"不二庵,就是这座寺院的前身。而'不二'二字,正是建文帝出家后的法名。"
"难道说……"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,不敢置信地看着老僧,"这座寺院是建文帝建立的?"
"不错,建文帝回国后,就隐居在这座寺院,直到去世。"老僧缓缓说道,"而这些日记和遗物,由历代住持秘密保管至今。"
我的头脑一片混乱,如果这一切属实,那么明朝第一谜案就此揭开!建文帝并非死于宫火,而是成功出逃,辗转多国,最终回到故土,在这座偏僻的山寺中度过余生。
"但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这些?"我不解地问。
"因为时机已到。"老僧深吸一口气,似乎在为即将揭露的秘密做准备,"建文帝在遗嘱中说,待到他去世五百年后,可将真相告知世人。而今年,正好是他去世五百周年。"
老僧走到石室的一角,指着地面上一块看似普通的石板:"他就长眠于此。"
我跟着老僧的指引,看到地上有一块普通的石板,上面没有任何标记。如果不是老僧指出,我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特殊之处。
"历代住持都守口如瓶,为何现在要公开这个秘密?"我仍然不解。
"因为建文帝在遗嘱中说,待到他去世五百年后,可将真相告知世人。"老僧重复道,"他认为,五百年后的中国,朱明已逝,新的朝代也已更迭,昔日的恩怨情仇已成历史,公开真相不会再引起任何政治风波。而今年,正好是他去世五百周年。"
从那天起,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。
从那天起,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。建文帝的秘密如同一把钥匙,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之门,而我,则成为了这个惊天秘密的见证者与传承人。每一页泛黄的日记,每一件珍贵的遗物,都在向我诉说着一个尘封五百年的传奇故事。我不禁要问:这位流落天涯的帝王,在他漫长的流亡岁月中,究竟经历了什么?他的内心世界,又有着怎样的波澜壮阔?
随着对悟元师父的了解加深,我开始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。他对建文帝事迹的了解如此详尽,对历史细节的把握如此精准,远超一般学者,甚至连那些没有记载在史书上的细节都了如指掌,仿佛亲历一般。这位神秘的老僧,究竟是什么人?
"师父,冒昧问一句,您和这座寺院,究竟是什么关系?您又是如何得知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的?"一天晚上,我终于忍不住问道。
老僧微笑不语,神色平静如水,只是示意我继续查看木箱中的物品。在他的引导下,我发现了更多惊人的证据:一封明英宗写给"不二庵主"的亲笔信,信中提到"先帝隐迹之事,朕已知晓,然念及皇族血脉,愿护先帝安度晚年,特拨御库黄金百两,岁岁供奉,以示朕对祖宗之敬";还有一张建文帝晚年的画像,虽然画中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僧,但仔细辨认,眉宇间仍能看出年轻时的影子,与官方画像中的建文帝有几分神似。
更令我震惊的是,我在箱底发现了一份详细的系谱表,上面记载了不二庵历代住持的名字和来历。悟元师父指着最上面的名字说:"这是建文帝出家后的法名——不二。"
系谱表显示,不二法师于正统十三年圆寂,终年七十二岁。而后,寺院由他的弟子继承,代代相传,一直到现在的悟元师父——第二十三代住持。
"您是建文帝的传人?"我惊讶地问。
"不仅如此。"老僧从怀中取出一方小印,正是系谱表上记载的历代住持信物,"我是这座寺院的第二十三代住持,也是奉命守护这个秘密的最后一人。"
"最后一人?"我不解地问。
"建文帝在遗嘱中说,五百年后,世道已变,朱明已逝,可将真相公之于世。而今正值其去世五百周年,是该让历史真相重见天日的时候了。"老僧的语气庄重而肃穆。
我仔细回想着这几天看到的所有证据:建文帝的日记、玉玺、亲笔信,以及英宗皇帝的回信,再加上系谱表和画像,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惊人的事实——建文帝确实逃过了靖难之役,并最终回到江南,在这座名为不二庵的寺院中度过了晚年。
"师父,您打算如何公布这个秘密?这将彻底改写明史啊!"我激动地说。
"非我公布,而是由你。"老僧意味深长地看着我,"你是历史学者,又与此事有缘,理应由你将真相告诉世人。建文帝在遗嘱中说,希望由一位无私无畏的史学家来完成这个使命。我观你为人正直,学识渊博,正是合适的人选。"
我受宠若惊:"我?这责任太重大了!万一学界不认可怎么办?"
"不必担忧,我会助你一臂之力。"老僧说着,从石室的暗格中取出一本厚重的古籍,封面上用金线绣着"出亡录"三个大字,"这是建文帝亲笔所著《出亡录》,详细记载了他出逃后的所有经历,包括在印度的三十年,以及回国后的生活。此书只有一册,从未外传。"
我小心翼翼地接过这本珍贵的史料,仿佛捧着一块无价之宝。书页已经泛黄,但保存完好,没有任何虫蛀或水渍的痕迹。翻开第一页,只见上面写着:"予乃朱元璋之孙,明朝建文帝朱允炆。今留此书,记予一生浮沉,以正视听。若后世有缘人得见此书,当知天下兴亡,皆有定数,不必强求。"
接下来的内容更是惊人。建文帝详细记录了他如何在宫火中脱身,在忠臣徐景昌和一些宫女太监的帮助下化装成和尚逃出南京城。他还描述了逃亡途中的艰辛,以及在云南、缅甸和印度的见闻。
"建文四年七月初三夜,燕王兵临城下,内外勾结,大势已去。徐辉祖战死,忠臣良将所剩无几。方孝孺劝吾自焚以全社稷尊严,然吾不忍就此而亡。景昌言,若天子亡,则天下将大乱,不如暂避其锋,以待时机。吾思之再三,决定微服出宫。是夜,吾换上太监服饰,由景昌引路,从宫中密道脱身。临行前,命宫女在寝宫中纵火,以惑众人耳目。不料火势太大,竟烧毁大半宫殿,皇后及多名宫女葬身火海。每思及此,痛彻心扉,悔恨终生。"
最令人动容的是,他在书中表达了对朱棣的复杂情感——既有被迫逃亡的愤怒,也有对叔父政治才能的钦佩,更有对朱明江山的深切牵挂。
"永乐五年春,闻叔父派郑和下西洋,扬我中华国威。此举魄力非凡,远非我当年所能及。回想当年削藩之举,操之过急,未能体察叔父之能,以致酿成大祸,实乃咎由自取。然叔父起兵作乱,残害忠臣,亦非明君所为。今思往事,双方皆有过错,奈何天意如此,非人力所能挽回。"
"永乐十八年,闻叔父修建紫禁城,规模宏大,气势恢宏。又修《永乐大典》,网罗天下典籍,此乃盛世文治之象。叔父虽以非正统手段登基,然治国有方,恤民爱才,不失为一代明君。若我当年能有叔父之才,或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然历史已成定局,空悲叹亦无益,唯有放下执着,看淡荣辱,方能得大自在。"
建文帝还记录了他在印度期间研习佛法的心得,以及对人生、权力的深刻思考。他在书中多次提到,失去皇位反而让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,能够以普通人的身份感受世间百态。
"予居天竺期间,遍访名僧,参研佛法。始知人生如梦,富贵如浮云。昔日龙椅上,忧心天下事;今朝茅庵中,一任云卷舒。失之桑榆,收之东隅,人生浮沉,何必强求。若非此番劫难,予岂能看破红尘,悟得此理?"
更令人惊讶的是,书中记载建文帝回国后,曾微服私访过南京、北京等地,亲眼目睹了永乐、宣德、正统年间的社会风貌。
"正统七年夏,微服至南京,观故宫旧址。物是人非,恍如隔世。昔日龙楼凤阁,今已改建;当年争权夺利的大臣,也都作古。唯有秦淮河水依旧流淌,见证着历史的沧桑。行至午门前,忆起当年登基情景,恍如昨日。然而,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天子,早已被岁月磨去了棱角,只剩下一个看破红尘的老僧。"
"正统八年春,路过应天府一处茶楼,听闻说书人正在讲述'靖难之役'。他将我描述成昏君,将叔父塑造成英雄。台下众人无不叹服,为燕王的'忠义'喝彩。我坐在角落,听着自己的'恶行',不禁莞尔。历史终究是由胜利者书写,而我,已成了那个被妖魔化的失败者。然细想之下,天下苍生只关心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,至于帝王更替,不过是风云变幻,于他们何干?"
《出亡录》的最后部分,记载了建文帝回到栖霞山后的生活:
"正统六年,予归栖霞山,建不二庵,日诵经礼佛,悠游山水间。每逢初一十五,必施粥于山门,济贫苦之民。虽不能如在位时那般泽被苍生,然一粥一饭,亦是善缘。英宗帝似已知晓予之下落,然并未加以追究,反而每年暗中派人送来黄金百两,以作香火之资。此情此义,予深为感动。"
"天顺二年,予已七十有六,感觉时日无多。回首一生,荣辱沉浮,恍如一梦。幼时在宫中长大,少年继承大统,中年流落异国,晚年归隐山林。若非亲历,谁能相信这是一个人的一生?然细思之下,无论帝王将相,还是平民百姓,生老病死,皆是常态,无可逃避。唯有看破红尘,方能自在。予今将毕生经历著为《出亡录》一书,非为自辩,只愿后人知晓,历史从不只有一种可能。五百年后,当朱明已成历史,天下早已更易,或可将此书公之于世,以正视听。"
我通宵达旦读完了整本《出亡录》,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这不仅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,更是一位亲历者对那段动荡历史的真实记录,其史学价值无可估量。更重要的是,这本书展现了一个与正史完全不同的建文帝形象——不是那个懦弱无能的傀儡皇帝,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喜怒哀乐的真实人物,一个在逆境中成长、最终看破红尘的智者。
第二天清晨,悟元师父带我来到寺院后山的一处僻静所在。穿过一片竹林,爬上一段陡峭的石阶,来到一个隐蔽的小平台。那里有一座不起眼的小石塔,塔基已被青苔覆盖,塔身上没有任何文字。四周古树参天,鸟语花香,宁静祥和。
"这就是建文帝的衣冠冢。"老僧说,"他真正的陵寝在石室地下,只有历代住持知晓。按照他的遗嘱,他希望死后葬在这里,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融为一体。"
我恭敬地向石塔行礼,心中感慨万千。一代天子,辗转流离,最终在这偏远山寺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他经历了从权力巅峰到流落异国的巨大落差,却最终看破红尘,在平淡中寻得了内心的宁静。
"师父,这些证据太过珍贵,我们该如何向学界公布?恐怕会遭到质疑。"我担忧地问道。
"我已准备多年。"老僧从袖中取出一个现代的U盘,这与他古朴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,"这里面有所有文物的高清照片,包括日记、玉玺、信件的扫描件,以及《出亡录》的全文影印本。"
他顿了顿,继续说道:"更重要的是,这里还有DNA检测报告——我们从建文帝遗留的发丝和指甲中提取了DNA,与明太祖陵出土的遗骸进行了比对,结果显示为直系血亲关系,证实了这些遗物确实属于建文帝朱允炆。"
我震惊地接过U盘:"您已经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?包括DNA检测?这需要专业的实验室和技术啊!"
老僧神秘地笑了笑:"五百年的等待,就是为了这一刻。我们有自己的渠道,确保这些检测都是在最权威的机构进行的,只是没有公开身份。建文帝希望后人知道真相,不是为了替他平反什么,而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。他在《出亡录》最后写道:'予一生荣辱浮沉,已无憾矣。今留此书,非为自辩,只愿后人知晓,历史从不只有一种可能。'"
老僧的话让我陷入沉思。历史从不只有一种可能——这句话意味深长。正史记载建文帝死于宫火,但实际上他逃脱了,辗转多国,最终回到故土。这完全改变了我们对明初历史的认知,也为研究明代政治、宗教和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在老僧的指导下,整理了所有关于建文帝的史料证据,并撰写了一篇详尽的学术论文。论文中,我详细分析了建文帝的日记、《出亡录》和其他遗物的真实性,以及这些发现对明史研究的重大意义。
"师父,我有一个疑问。"一天晚上,我在整理资料时突然问道,"建文帝在位仅四年,为何会有如此高深的佛学造诣?《出亡录》中的一些佛理论述,甚至连我这个现代人都难以理解。"
老僧微笑道:"这正是最有趣的部分。建文帝在位时,虽然年轻,但极为好学,精通儒释道三家。他在印度的三十年,又深入研习了梵文原典,融会贯通。《出亡录》中的佛理论述,大多是他晚年所得,已是大彻大悟之境界。"
"还有一点我不明白。"我继续问道,"建文帝既然活到了天顺年间,为何没有尝试联系当时的皇帝?按理说,英宗和他已经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了。"
"他确实联系过。"老僧说,"《出亡录》中提到,英宗帝曾派人暗中拜访过他,甚至提出要恢复他的皇位。但建文帝已经看破红尘,拒绝了这个提议。他认为,国家需要稳定,而不是再次陷入权力斗争。英宗深受感动,承诺会保守这个秘密,并每年暗中供奉黄金百两,作为香火之资。"
"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!"我惊叹道,"这完全改变了我们对明代皇室关系的认知。"
"历史的真相,往往比想象中更加复杂。"老僧意味深长地说。
公布前夕,我忐忑不安:"师父,这个发现太过震撼,会不会遭到学界的质疑和反对?毕竟它挑战了几百年来的正统史观。"
"真金不怕火炼。"老僧镇定自若,"我们有确凿的物证和文献,还有DNA比对结果。更重要的是,这个发现填补了历史的空白,解开了困扰学界数百年的谜团。如果有人质疑,我们欢迎他们来栖霞山亲自考察。"
果然,当我在国际明史研讨会上公布这一发现时,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会场一片哗然,许多资深学者当场表示质疑。
"林博士,你的发现太过惊人,几乎颠覆了我们对明初历史的认知。"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站起来说,"你能否提供更多证据,证明这些日记和《出亡录》确实出自建文帝之手?"
我冷静地展示了准备好的证据:"我们有建文帝的御玺原件,有他的亲笔信,有历代住持的系谱表,还有DNA比对结果。这些都已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,证实其真实性。此外,《出亡录》中提到的许多历史细节,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,几乎不可能是后人伪造的。"
"这些文物是如何保存至今的?"另一位学者问道。
"栖霞山不二庵的历代住持,肩负着保护这个秘密的使命。"我解释道,"根据建文帝的遗嘱,这个秘密只能在他去世五百年后公开。而今年,正好是他去世五百周年。"
会后,各国史学家纷纷前来栖霞山考察,对所有证据进行了严格的鉴定。文物专家确认玉玺为真品,笔迹专家证实日记和《出亡录》确实出自同一人之手,碳14测定证实这些文物的年代与明代相符,而DNA测试更是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。
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东亚史专家在考察后感慨道:"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最重大的发现之一。它不仅解开了建文帝的去向之谜,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明代政治、宗教和中印文化交流的宝贵第一手资料。《出亡录》中记载的建文帝在印度的见闻,填补了明代中印关系史的重要空白。"
一时间,"建文帝在栖霞山终老"的消息轰动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。各大媒体争相报道,栖霞山一下子成了热门旅游景点,游客络绎不绝,都想一睹建文帝隐居的地方。不二庵也因此得到了政府的保护和修缮,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而我,也因此成为了国际知名的明史专家,受邀在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讲学。我的博士论文《建文帝出亡录研究》获得了极高的评价,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。每当有人问起这个发现的过程,我总是由衷感谢那位神秘的老僧悟元,是他将这个秘密传递给了我,让我有幸成为这段尘封历史的见证者。
然而,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。就在我的研究成果公布后一个月,我再次回到栖霞山,想要向悟元师父汇报学界的反响,却发现寺院已经易主,新住持是一位年轻的和尚,他声称从未听说过悟元这个人。
"这里一直是我们常住寺院,从未有过'悟元'这个法名的和尚。"年轻住持困惑地说。
更奇怪的是,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间藏有建文帝遗物的石室了。我按照记忆中的路线,穿过竹林,来到悬崖边,却只看到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,哪里有什么石室的踪影?
正当我困惑不解时,一位在山上采药的老人向我走来:"小伙子,你在找什么?"
"我在找一间石室,上面刻着'不二法门'四个字的。"我急切地问道。
老人疑惑地看着我:"这栖霞山上,从没有这样一间石室啊。不过,山上确实曾有一座叫'不二庵'的古寺,据说是明朝时建的,但早在百年前就已废弃了。近年才有新僧人来此重建寺院。"
"那悟元师父呢?就是那位年近九十的老和尚?"我急切地问。
老人摇摇头:"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。我在栖霞山住了六十多年,认识山上的每一个和尚,却从未见过你说的这位老僧。"
老人顿了顿,又补充道:"不过,栖霞山上确实流传着一个传说,说这里曾住过一位明朝的贵人,据说是被迫出家的,很有可能是个皇族。每到月圆之夜,山上的老松树下,会有一个身穿龙袍的影子在徘徊。"
我心中一震,回想起与悟元师父相处的点点滴滴,他那超乎寻常的学识,对建文帝事迹的了如指掌,以及那种难以言喻的威严气质……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浮现在脑海:难道悟元师父就是……
但这个念头太过荒谬,我很快将它抛诸脑后。无论悟元师父是谁,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——将建文帝的真相公之于世,解开了这个困扰中国历史数百年的谜团。
就在我准备离开栖霞山的那天晚上,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我困在了山上。我不得不在一座废弃的小茅屋中避雨。雨声淅沥,山风呼啸,我独自一人坐在昏暗的茅屋中,不禁想起了这几个月来的种种经历。
就在这时,一道闪电划过天际,照亮了整个茅屋。在那一瞬间的光明中,我看到茅屋的墙上挂着一幅画像,画中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僧,神态安详,嘴角带着一丝微笑。画像下方题着四个字:"不二法师"。
闪电过后,茅屋重又陷入黑暗。我急忙点燃随身携带的打火机,想要再看清那幅画像,却发现墙上空空如也,哪有什么画像?
我揉了揉眼睛,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。正当我困惑不解时,忽然发现茅屋角落里有一个小木盒,看起来十分眼熟。我颤抖着手打开木盒,里面放着一封信和一块玉佩。
玉佩上刻着"允炆"二字,而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——林墨。
我急忙拆开信,里面只有简短的几行字:
"林墨贤契:
缘分已尽,老僧当归去矣。建文之谜,今已公诸于世,吾心甚慰。栖霞山不二庵,自今而后,不复存在。然真相已明,史册可正,此乃天意。他日若有缘,再聚栖霞。
悟元合十
永和二年春"
我惊讶地看着信上的落款——永和二年?这是什么年号?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永和年号啊!
正当我困惑不解时,一阵清风吹过,信纸上的字迹渐渐模糊,最后竟完全消失了。只留下那块刻有"允炆"二字的玉佩,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里。
第二天清晨,雨过天晴。我再次来到那片曾有石室的地方,发现昨晚的暴雨冲刷出了地下的一些遗迹。在考古专家的帮助下,我们挖掘出了一座古老的地宫,里面安放着一具棺椁。棺椁上刻着"不二法师"四字,内有一具身着僧袍的遗骸,保存完好。
DNA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:这具遗骸确实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直系血亲关系,证实了这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遗体。
而在遗骸旁边,我们还发现了一块完整的墓志铭,上面刻着:
"大明建文帝朱允炆,讳允炆,明太祖朱元璋嫡长孙,惠帝朱允炆之子。洪武三十一年继统大宝,在位四年。建文四年,燕王朱棣起兵靖难,帝微服出亡,辗转云南、天竺等地。正统六年归隐栖霞山,建不二庵,精研佛法。天顺七年七月十五日圆寂,享年七十二岁。"
墓志铭的最后一段文字尤为令人动容:
"帝天资聪颖,少有远志。即位后厉行改革,削藩以强国,意在开创盛世。然天不遂人愿,遭遇靖难之役,被迫逃亡。出亡期间,遍历诸国,深入研习佛法,终悟大道。晚年归隐栖霞,日诵经典,普济群生。帝一生荣辱浮沉,如梦如幻,终能放下执着,看破红尘。死后葬于此,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融为一体。愿后世子孙,铭记历史,珍爱和平。"
墓志铭的落款是:"永乐皇帝朱棣敬立"。
这最后一行字,令所有人震惊不已。难道说,朱棣最终知道了建文帝的下落,不仅没有加害于他,反而为他立下墓志铭?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永乐帝的认知!
更奇怪的是,墓志铭上提到的天顺七年,正史记载这一年明代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重大的事件。难道说,史书有意回避了建文帝的死讯?
这些新发现再次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。有学者认为,墓志铭可能是建文帝的支持者伪造的,意在为他平反;也有学者相信,这确实是朱棣所立,证明他晚年对篡位一事心怀愧疚。
无论真相如何,建文帝的谜团,终于在五百年后得到了解答。而那位神秘的老僧悟元,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,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多年后,当我已经成为享誉国际的明史专家,受聘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时,我仍然时常思考那段奇异的经历。每当我看到那块刻有"允炆"二字的玉佩——那是我唯一能证明那段经历确实存在的物证——我就会想起悟元师父最后留下的那封信,和那个不存在的"永和"年号。
有一天,我在整理资料时,无意中翻到了一本古籍中的一段记载:
"传说建文帝在天竺修行时,曾立誓:若有一日能够回归故土,必建立'永和'年号,取'永世和平'之意。然此愿终未能实现。"
我恍然大悟,原来"永和"是建文帝未能实现的年号愿望。那么,那位神秘的老僧悟元,究竟是谁?是建文帝的转世?是守护秘密的最后一位住持?还是某种超越时空的存在?
这个谜团,或许永远不会有答案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:建文帝朱允炆,这位被历史尘埃掩盖的明朝皇帝,他的故事,他的智慧,他的人生哲学,已经通过《出亡录》传递给了后世。而我,有幸成为了这段尘封历史的见证者和传播者。
正如建文帝在《出亡录》最后所写:"历史从不只有一种可能。"也许,这就是他留给世人最宝贵的遗产。
明朝第一谜案,终于在五百年后得到解答。建文帝并非死于宫火,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流亡生涯,最终回到故土,在栖霞山的不二庵中安度晚年。这段尘封的历史,不仅见证了一个帝王的沉浮,更折射出人生无常与历史多元的永恒真理。而那位神秘的老僧悟元,或许是穿越时空的守护者,又或许是某种冥冥之中的安排,引导我揭开这层尘封已久的面纱。正如建文帝所言:"历史从不只有一种可能。"这或许是对这场跨越五百年时空的奇遇,最好的诠释。
声明:本篇故事为虚构内容,如有雷同纯属巧合,采用文学创作手法,融合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元素。故事中的人物对话、情节发展均为虚构创作,不代表真实历史事件。